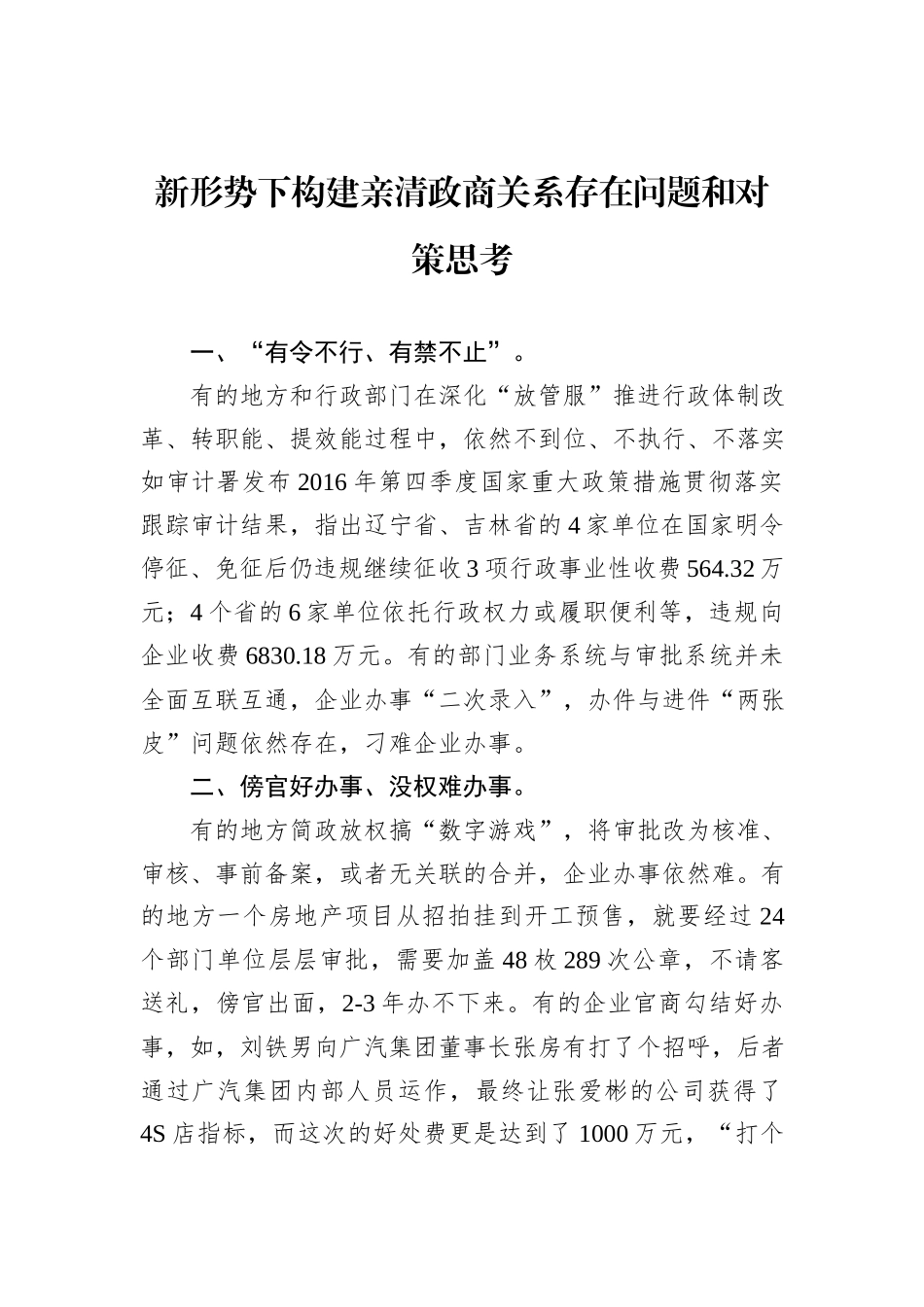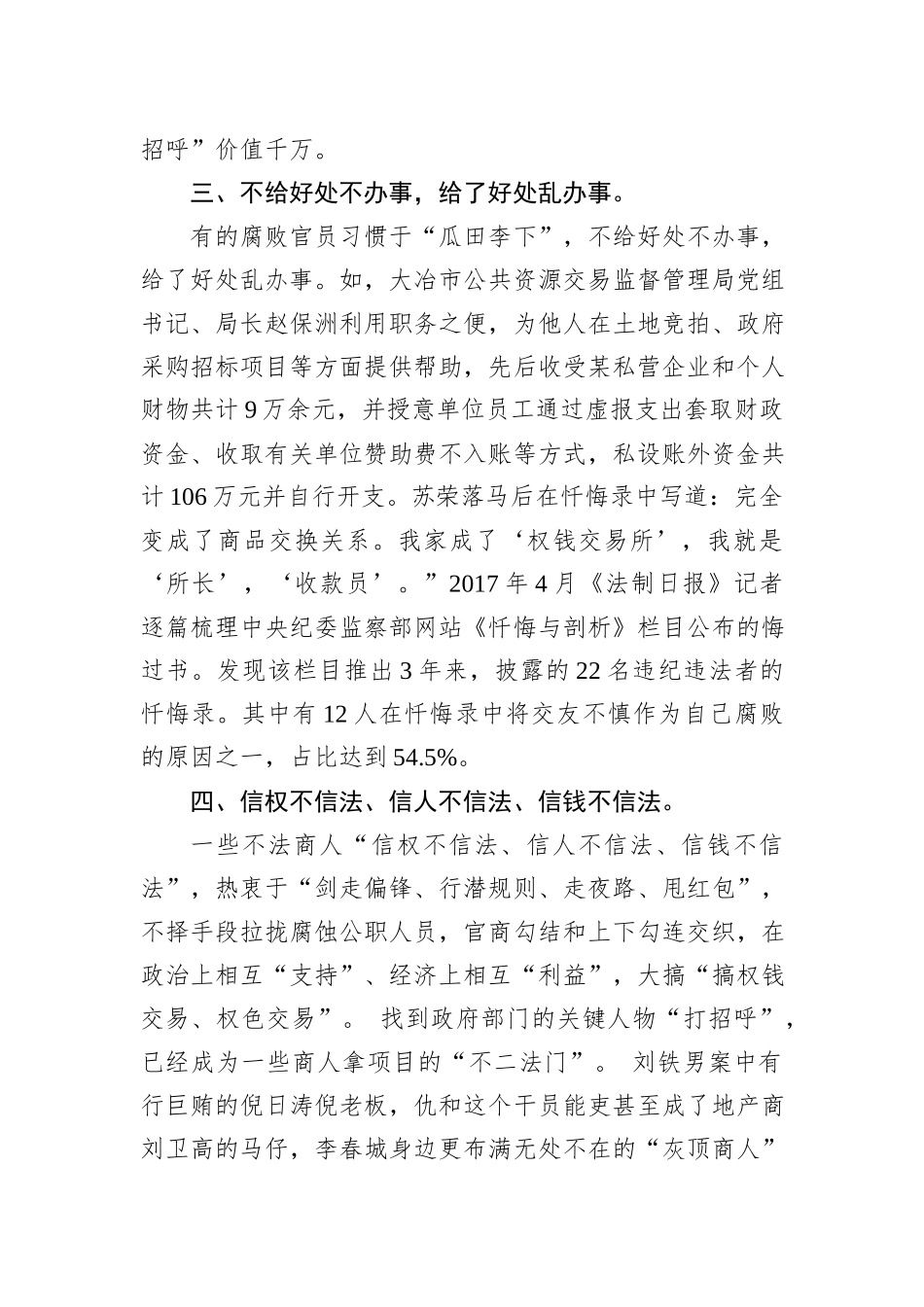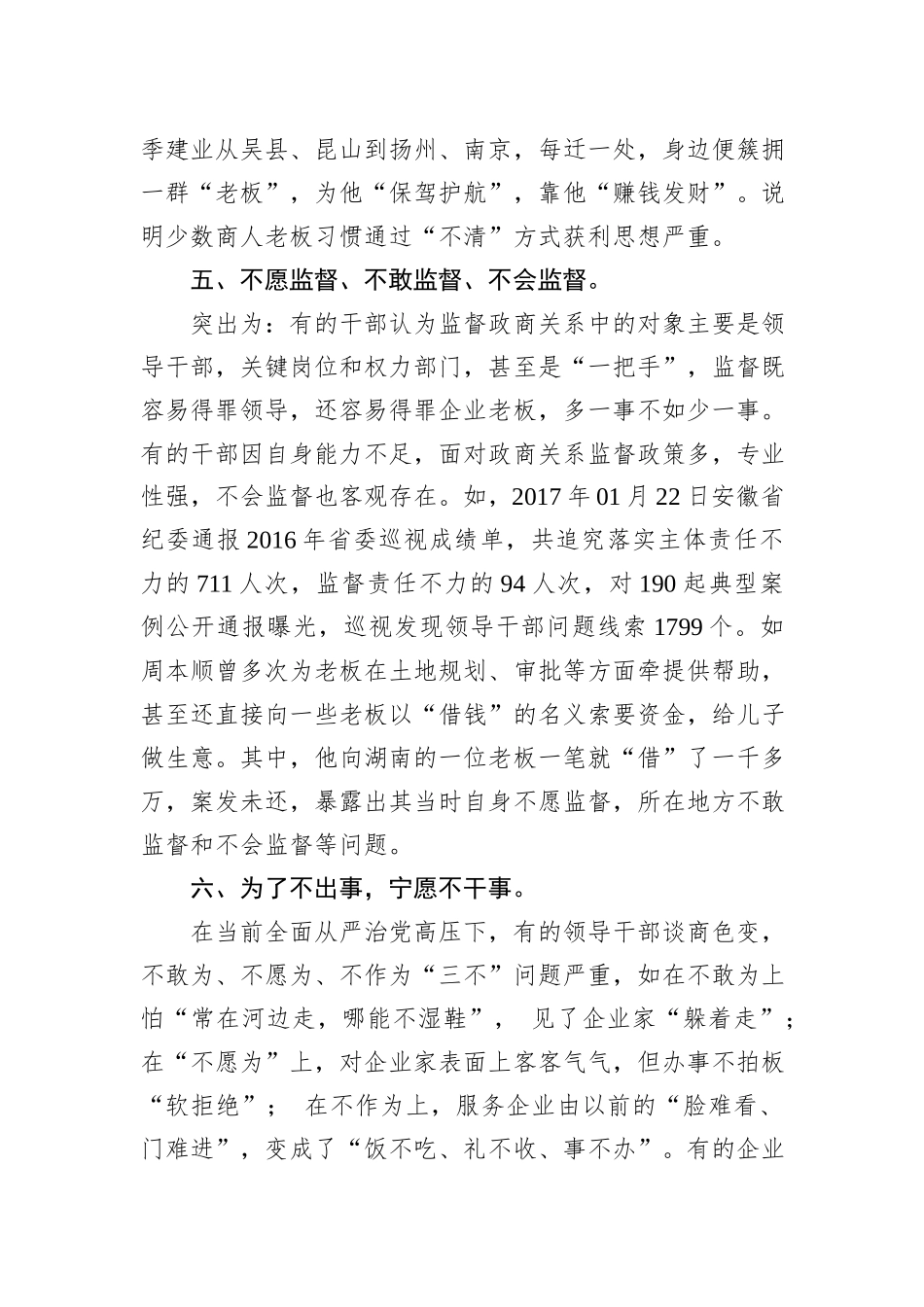新形势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存在问题和对策思考一、“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”。有的地方和行政部门在深化“放管服”推进行政体制改革、转职能、提效能过程中,依然不到位、不执行、不落实如审计署发布 2016 年第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结果,指出辽宁省、吉林省的 4 家单位在国家明令停征、免征后仍违规继续征收 3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564.32 万元;4 个省的 6 家单位依托行政权力或履职便利等,违规向企业收费 6830.18 万元。有的部门业务系统与审批系统并未全面互联互通,企业办事“二次录入”,办件与进件“两张皮”问题依然存在,刁难企业办事。二、傍官好办事、没权难办事。有的地方简政放权搞“数字游戏”,将审批改为核准、审核、事前备案,或者无关联的合并,企业办事依然难。有的地方一个房地产项目从招拍挂到开工预售,就要经过 24个部门单位层层审批,需要加盖 48 枚 289 次公章,不请客送礼,傍官出面,2-3 年办不下来。有的企业官商勾结好办事,如,刘铁男向广汽集团董事长张房有打了个招呼,后者通过广汽集团内部人员运作,最终让张爱彬的公司获得了4S 店指标,而这次的好处费更是达到了 1000 万元,“打个招呼”价值千万。三、不给好处不办事,给了好处乱办事。有的腐败官员习惯于“瓜田李下”,不给好处不办事,给了好处乱办事。如,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、局长赵保洲利用职务之便,为他人在土地竞拍、政府采购招标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,先后收受某私营企业和个人财物共计 9 万余元,并授意单位员工通过虚报支出套取财政资金、收取有关单位赞助费不入账等方式,私设账外资金共计 106 万元并自行开支。苏荣落马后在忏悔录中写道: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。我家成了‘权钱交易所’,我就是‘所长’,‘收款员’。”2017 年 4 月《法制日报》记者逐篇梳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《忏悔与剖析》栏目公布的悔过书。发现该栏目推出 3 年来,披露的 22 名违纪违法者的忏悔录。其中有 12 人在忏悔录中将交友不慎作为自己腐败的原因之一,占比达到 54.5%。四、信权不信法、信人不信法、信钱不信法。一些不法商人“信权不信法、信人不信法、信钱不信法”,热衷于“剑走偏锋、行潜规则、走夜路、甩红包”,不择手段拉拢腐蚀公职人员,官商勾结和上下勾连交织,在政治上相互“支持”、经济上相互“利益”,大搞“搞权钱交易、权色交易”。 找到政府部门的关键人物“打招呼”,已经成为一些商人拿项目的“不二法门”。 刘铁男案中有行巨贿的倪日涛倪老板,仇和这个干员能吏甚至成了地产商刘卫高的马仔,李春城身边更布满无处不在的“灰顶商人”季建业从吴县、昆山到扬州、南京,每迁一处,身边便簇拥一群“老板”,为他“保驾护航”,靠他“赚钱发财”。说明少数商人老板习惯通过“不清”方式获利思想严重。五、不愿监督、不敢监督、不会监督。突出为:有的干部认为监督政商关系中的对象主要是领导干部,关键岗位和权力部门,甚至是“一把手”,监督既容易得罪领导,还容易得罪企业老板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有的干部因自身能力不足,面对政商关系监督政策多,专业性强,不会监督也客观存在。如,2017 年 01 月 22 日安徽省纪委通报 2016 年省委巡视成绩单,共追究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的 711 人次,监督责任不力的 94 人次,对 190 起典型案例公开通报曝光,巡视发现领导干部问题线索 1799 个。如周本顺曾多次为老板在土地规划、审批等方面牵提供帮助,甚至还直接向一些老板以“借钱”的名义索要资金,给儿子做生意。其中,他向湖南的一位老板一笔就“借”了一千多万,案发未还,暴露出其当时自身不愿监督,所在地方不敢监督和不会监督等问题。六、为了不出事,宁愿不干事。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高压下,有的领导干部谈商色变,不敢为、不愿为、不作为“三不”问题严重,如在不敢为上怕“常在河边走,哪能不湿鞋”, 见了企业家“躲着走”;在“不愿为”上,对企业家表面上客客气气,但办事不拍板“软拒绝”; 在不作为上,服务企业由以前的“脸难看、门难进”,变成了“饭不吃、礼不收、事不办”。有的...